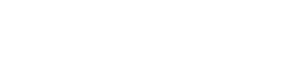
年 月 日 ENGL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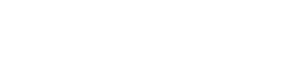
年 月 日 ENGLISH
金碚:探索区域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相容机制
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是主题,但其内涵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一个曾经十分贫穷、生产力低下的国家,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以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地球上踏上自己的巨大“足迹”,让整个世界因此而面貌大变。与此同时,中国这一体量庞大的经济巨人,也将面临人类发展的终极问题:要让自己唯一的国土家园变得怎样?以至要让“地球村”变成怎样?我们可以称之为“巨人之惑”:当人类发展成具有超级能力的种群之后,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却反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大的人类是否正在破坏自己的生存之地?
一、绿色发展理念触及人类发展的价值核心
产业活动与环境保护(或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相斥、相容、相促。“相斥”是指,生产活动会严重破坏环境,如果要保护生态环境,就不得进行这样的生产活动,而如果要进行这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付出很大的环境代价,即两者相互排斥,只能取此舍彼。“相容”是指,生产活动能够在一定的环境容量中进行,可以不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处于自然界可自我净化的范围之内,或者可以进行环境还原或修复,反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构成对生产活动的完全禁止,两者可以共存。“相促”是指,产业活动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环境改善,两者间是互利共赢关系。
导致这三种不同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物源性、技术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物源因素是指,生产的物质性质,例如,用人力、畜力等作为动力,或采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作为能源,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影响。技术因素是指,生产流程和工艺及其先进程度,例如,煤发电是否采用脱硫等环保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影响。社会因素是指,经济体制、管理水平、政策行为等,导致产业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
在现实中,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相斥、相容、相促的各种复杂关系,期间,物源、技术和社会因素都会发生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上三种关系及三种因素的关系,也会发生某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一般来说,相斥性逐渐减少,相容性尤其是相促性逐步增强;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比物源性因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经济带,正在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化。
二、成本竞争与环境友好的产业技术选择
生产活动原本是人类发展中的工具性行为,即通过生产活动,使更多原本(对人类)无用之物转变(加工制造)为有用之物,使原本人类难以居住和到达的地方变为(建设为)可以方便到达和宜于居住之地。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原来是朴素和明了的。但在人类获取巨大经济成就的时候,一些地方怎么反而会变得环境恶劣了呢?人们为什么要做同自己的初衷目标背道而驰的事情呢?
在经济发展中,产业进步的基本路径是沿着寻求和获得资源与实现物质转换(即加工制造)的低成本方向演化的。即尽可能用自然储量多、获取和加工比较容易的物质,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成本竞争;一项新技术能否被采用于大规模生产,也必须解决降低成本的问题,以达到其经济性要求,否则就无法被广泛使用。当工业化水平不高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往往更注重其成本竞争要求,而难以更多地注重其环境友好性,往往不得不以牺牲环境来获得成本竞争优势。此时,生产与环保之间的相斥性非常突出,将生产控制在同环境相容的范围内都得进行很大的努力和做出困难的抉择。权衡中往往“紧迫性超过了重要性”,其后果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实际上是以很高的环境成本求得较低的企业生产内部成本,而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却被在技术选择中降低了其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从人类发展的价值准则看,环境保护是更重要的,具有根本性价值,但从市场竞争来看,产业增长所需要的企业生产低内部成本要求却更具紧迫性和工具理性意义。因此,人们以牺牲目的为代价,追求手段的更强大。后果是,手段更强大有力了,但离目标却更远了。目前,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已超过了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度,必须进行生态修复,才能保护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重要性”最终成为更大的“紧迫性”“目的”最终显示了高于“手段”的重要性。
就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而言,进行生态修复和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实际上归结为两个经济学含义:一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即生产企业必须承担全部的环保责任,因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而完全失去竞争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即企业无力承担环保责任)将被淘汰和禁止,因为那意味着得不偿失,事与愿违;二是采取环境友好的技术路线,或者发展本身具有促进环境改善的产业。前者主要表现为让具有较强成本竞争优势的产业,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成本竞争优势。企业(及产业)可以通过自我消化(降低利润率)和(或)转移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来应对因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而导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压力。后者主要表现为提高技术水平或改变技术路线,从而提高技术对环境的有利影响,降低以至消除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激励相容
人类经济发展的目的是,通过与自然的互动,使自己能够生活在更安全、更适宜、更富足、更愉快的环境和状态中。这是产业发展的价值目标,即本原意义。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方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机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的主要是体现工具理性的行为和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理性倾向。所谓工具理性或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生产活动的直接目的和动力,并非其真正的或本原的价值目标,而是工具目标,例如收入、财富、利润、GDP及其增长率,以至企业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扩张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目标,只能以追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财富最大化的动力(欲望和偏好)来实现。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大多是工具性目标。
从理论上说,工具理性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价值目标的,而且,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不经历工具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实际上无法实现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这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人类发展无可替代的道路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完全沉迷于工具主义中,而忘却本原的价值目标,就会走向发展的迷途,失去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例如,在产业发展中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危害健康和安全,就是典型的迷失价值目标而盲目地受工具主义理性驱使的现象。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将“工具”作为无度追求的“目标”。此时,所谓“业绩”或“政绩”已经成为虚幻之物,以致于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类发展目标。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丑恶现象,而且将越来越难以容忍。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人类没有建立起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激励相容的有效体制机制。当人类终于认识到由工具理性驱动的产业发展必须具有明确而坚持的价值理性(目标)方向时,必然将绿色发展作为可行的道路和模式选择。如前所述,绿色发展的核心含义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是以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友好主导的产业技术路线。为此,居民、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回答“工具理性如何导向价值目标”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需要有以下新思维:
第一,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及权衡。任何地区的政府都会有多项政策目标,尽管各个目标均很重要,但在政策清单中总有优先顺序的排列,也需要在各目标间做出权衡,有的重点执行,有的必须兼顾,也有的则不得不暂时缓行。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时,发展经济就是第一优先政策目标,尽管也应注重生态环境,但它毕竟难以作为第一优先目标,不得不居于“兼顾”类次序。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时,修复生态、保护环境就会上升为第一优先政策目标。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历程就体现了不同时期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调整。过去30多年,长江经济带是将经济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第一政策目标,而在这次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中,生态环境提升为第一优先政策目标,就反映了新时期须有新思维和新的优先目标这一政策抉择的客观规律。当然,确定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绝不意味着可以顾此失彼,而是必须对各政策目标进行合理权衡和安排。特别是,发展经济仍是重要目标,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提升长江流域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发展目标和进程,选择更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也使在实现各政策目标时,不仅要知之所为,而且要具有明确的法规性依据。
第二,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的激励相容体制。任何地区的发展,在安排政策目标及其优先顺序时,都必然涉及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即有些政策目标更倾向于体现价值目标,例如,宜居、健康、安全、公益、就业与闲暇等;而有些政策目标更倾向于工具理性,例如,收入(GDP)、财富、竞争力等。价值目标具有终极重要性,但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工具理性的动力,工具理性通常要求有体现其意义的工具性政策目标。工具主义行为尽管是间接手段,但却是直接经济动力,尽管不可颠倒为最终目的,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目标。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否定工具主义理性,就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实际上也难以达到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当进行制度和政策安排时,使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之间形成激励相容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当进行由工具理性(追求工具理性目标)所驱使的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实现价值目标时,地区发展的道路和结果都会更具合意性。形象地说就是要力求做到:通过发展经济创造金山银山,使居民有条件能够在青山绿水蓝天中享受富足的生活。
第三,更自觉、有效地处理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地区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现实地体现为,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战略抉择总是需要有其决策主体,即谁来进行抉择?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在许多领域和方面都发挥着主导性或引导性作用,特别是在制定规划、确定重点、划分区位、提供优惠、项目审批等方面,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影响。而且,政府在有些方面的决策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是不可逆的。所以,各地政府总是处于必须审时度势,慎用巧用政策手段,应对复杂具体问题的处境。
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更倾向于工具主义理性,而政府作用所代表的主要是人类发展(社会和人民)的价值目标。所以,一方面,政府要持积极无为态度,即尊重市场的工具主义机理,不要破坏市场机制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相信,只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工具理性行为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可行有效方式之一,而且无可替代。政府应在完善市场体制、监管市场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在具体经济决策上,则应尽可能“无为而治”,避免自作聪明式的越位干预。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积极有为的行动,即更注重维护价值目标准则,实现区域发展的根本性民生目标和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例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所提及的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成全流域黄金水道等,就是政府必须积极有为实现的目标。